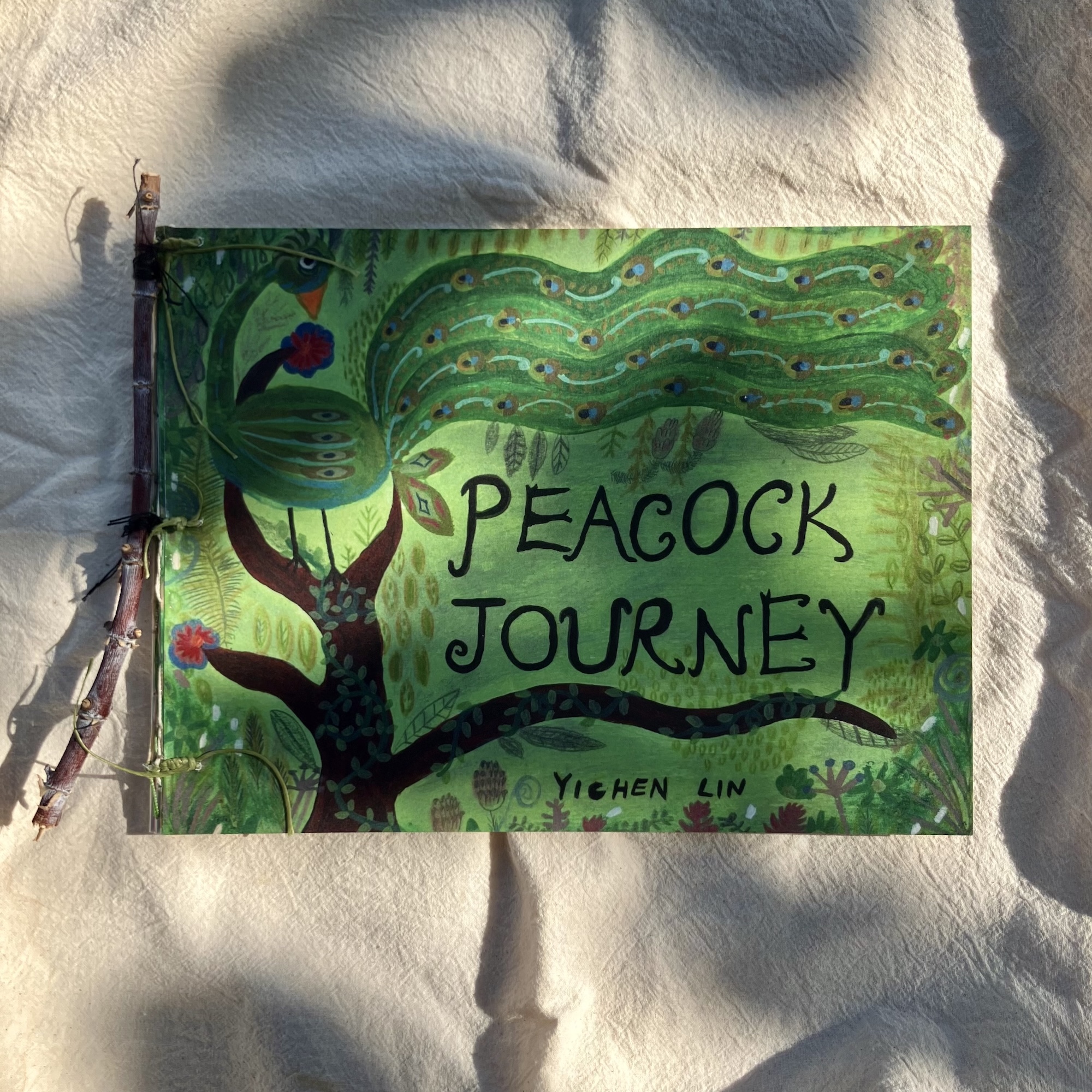第一部
1
我一直盯著你那雙攤在病床床單上的手。它們慘白得像張薄棉紙,彷彿是癱軟在河床上的樹根。我見過它們炙熱且充滿活力,從手掌到指腹佈滿傷疤的模樣。你笑稱自己是「燙傷王」。儘管圍裙上時時掛著一條擦拭布,餐館裡人聲鼎沸的時候,還是會急著一把握住鍋柄,伸出手指替小牛肋排或鱸魚翻面。被燙到了你也不會吭聲,照樣把手伸進滾燙的油裡,或者徒手替剛出爐的蛋糕脫模。
你說新的傷疤會帶走舊的,這句話是你從一位老師傅那裡聽來的,那人教會當時還是男孩的你做麵包。每當我觸摸那些粗糙的傷疤,你會咯咯發笑。我也總愛玩弄你食指的最後一個指節,它就像葡萄枝蔓般長了結節,然後我會要你重述它的變形史,聽了千遍也不厭倦。你說你當時年紀和我差不多,母親剛把絞肉機擺到桌子上,準備做醬糜。生鐵製的機器令你著迷,吸引你到桌旁坐下。母親允許你在她放肉塊時轉動握柄,只是沒想到某天你竟趁她暫時離開,把自己的手指也放進去絞了。大人們慌忙跑到鎮裡的大街上,請醫生開著小篷車到家裡為你檢查。在那個沒有人敢質疑醫生權威的年代,就算處方箋上寫著從白楊木上削下的兩塊木板,也不會有人多吭一聲。你咬緊牙根讓他把木板固定在指頭上,再用你父親的一條法蘭絨束腰帶緊緊包紮。然後他說一個月後再來檢查。
醫生把夾板取下時,那隻手指已經變成粉紅色的了,最後一個指節也歪向了左側。他說指頭保住了,但應該會免除兵役。父親一聽,皺起了眉頭大聲宣告你得跟所有人一樣從軍。說到這裡你總會搖頭嘆息:「他沒想到我會在阿爾及利亞待上二十個月。」然後繼續用那隻扭曲的手指與指甲刮洗鍋底。你說這樣比較容易處理難以清洗的角落。
你的食指放在刀背和擠花袋上的畫面仍歷歷在目,每個動作都像是在考適任證書般精準熟練。現在,我拉起那根食指,它就跟格子籠養出來的雞骨頭一樣輕盈細瘦。好幾次,我都想把指節掰直,但同時又為此感到恐懼。不,我不能這麼做。就算是在你死後,我也不能這樣對你。我想起小學時聽到的那則故事,至今還在我心裡留有一片陰影。那是關於一名禮儀師的故事,說的是朋友的禮儀師父親在為罹癌去世的大體整理儀容時,企圖把死者萎縮的腿骨拉直,沒想到骨頭卻應聲斷裂。他當然也被開除了。
我再次輕輕撫摸那雙手,期待看到它們移動,就算只是一毫米也好。但此刻它們就像在鍋子裡和馬鈴薯餅起舞後被你高掛在抽油煙機上的煎鏟。我打開床邊桌的抽屜,尋找那罐某年聖誕節我送你的香水。是卡朗(Caron)的謙謙君子(pour un homme)。「試試看,這瓶香水很適合那個年紀的男性。」里昂車站內的櫃姐這麼說。十二月二十五日的早晨,我替你刮了鬍子,你抓住我的手問:
「這什麼東西?」
「香水。」
「我從來沒用過。」
你勉強讓我在脖子上滴了幾滴,嘴裡不忘叨唸:「廚師不應該在身上噴香水。嗅覺和味覺會被搞壞。」你審慎地聞了聞,吐出一句:「可是你還是給我用了。」我把香水塗在手上,輕輕地按摩你的手指和手掌。
三天前,店裡的晚餐人潮離去後,因為還沒有睡意,我開著小貨車到城裡轉了一圈。我點了根駱駝牌香菸,轉開齊柏林飛船的〈No Quarter〉。那是我專屬的吵雜,你總是這麼說。冷冽的夜、冷清的街。有那麼一瞬間,我興起到和平咖啡館去喝個半品脫的興致。但想見你的心情凌駕一切。因此我還是一路開到醫院,在安寧緩和醫療科的門上輸入夜班護士芙羅倫絲給我的密碼。走廊是昏暗的橘色。你的房門半開著。藉著房裡透出的微光,我看到你那雙手造出的奇妙光影。你的雙眼緊閉,兩張手掌互相摩搓,彷彿正揉著甜塔皮的麵團,準備做甜點單上的檸檬塔。接著,你張開手指又掐又捏。是想把黏在手上的麵團捏掉嗎?我坐到床邊看著你,輕聲對你說:「爸,你的手還是一樣靈活。」我不期待任何回應,只希望你能聽見。我感覺到身後有個平穩的腳步靠近。
「他在做什麼?」芙羅倫絲小聲詢問。
「揉麵團。我本來以為是在做甜塔皮,但其實是麵包。他正在把黏在手指上的麵團清掉。」
「這手勢真美。」
「他什麼時候會離開我們?」
「決定權在他。」
2
這天晚上,我又聽到你和芙羅倫絲正在交談。那是個不需值班的週六。三個星期前,你還沒陷入昏迷的時候,你們經常在夜裡討論炊事。你詳述了你的每一道料理,用金黃葡萄酒和雞油菌一起烹煮的水波蛋,還有浸在糖漿裡的水蜜桃。你烹煮里昂魚糕的方式令她心醉。你不同意我說她這樣獻殷勤是為了騙取你的食譜。「她騙不到的,沒有人騙得到。」你仰天狂笑,又重申了幾次。
芙羅倫絲真的對你特別溫柔。我想,是你的堅毅感動了她。這六個月來,我在醫院裡做的任何事,她都睜一隻眼閉一隻眼。「這不能吃吧。」第一天看到醫院送來的餐點時,你就抗議了。所以我只能按你的意思為你送些「小便當」。你會小心地把紅格子餐墊攤在床舖上,我再幫你把靠背調整到你要的角度:馬鈴薯沙拉、芹菜佐雷莫拉醬、乾草燻火腿、油煎鹽燻鯡魚和馬鈴薯、酥皮肉醬。當然也不能忘記一小塊美味的起司:二十四個月熟成的康堤、埃普瓦斯或聖馬爾瑟蘭。你甚至要求一份雪花蛋白霜,就為了責怪我在裡頭放了「太多香草」。我還會用背包偷渡一小瓶酒和一個球形酒杯。你指定要紅酒,且必須帶有香料味和黑莓類的果實香味。
你完全陷入昏迷的前一晚,我用湯匙餵你。那是加了肉桂和檸檬的蘋果泥。當時的你已經無法說話,而且自那天起,你就再也沒有進食了。醫院為你準備了速眠安、止痛劑、鎮定劑和嗎啡調成的雞尾酒點滴。你啊,你老是說:「要是哪天我知道自己沒救了,一定不會拖太久。」沒想到你會花這麼多時間離開。
某天晚上,我問芙羅倫絲:「他為什麼遲遲不肯放手?」她沉默了好久,彷彿沒有盡頭。最後終於開口:「也許,是想多給你一點時間跟他道別?」這句話刺痛了我,從那天起,它就縈繞在我心裡。有時,我會覺得你陷入昏迷都是我的錯。也許是因為我日日哀怨或將成為孤子的悲痛,讓你情願承受皮肉之苦,遲遲不肯離去。某天,我貼近你的耳邊,想對你說:「爸,安心去吧。」但這幾個字卻頑固地卡在喉頭。
我拉開你的病人服,想為你擦些香水,看見你那佈滿血管、宛若大理石的皮膚,皮膚下的血液似乎已經凝結。你今晚就要走了。早上我動手準備情人節晚餐菜單上的蘑菇雞肉酥盒時就有預感。老顧客們指定這道你經常在二月十四日推出的特餐。首先是酥皮。把麵團切成兩份,用擀麵棍擀開後,再用圓形的模具切割。接著就是把酥皮盒子組好,抹上蛋汁。我對剛出爐的酥盒感到失望。酥皮不夠蓬鬆。不曉得該不該延長烘烤時間。那一刻,我多麼希望你就在身邊給我建議。我打開了窗戶,在罩著濃霧的寒夜裡啜了口咖啡,點燃一根菸。我心裡明白,你再也不會回到廚房裡對著我大聲叱罵了。
你從未教我做任何一道菜,或者應該說,從不像學校那樣教我。沒有食譜、沒有比例、沒有安排好的課程,我只能靠著雙眼和雙耳掠奪精華。當你說:「加鹽。」我會問:「怎麼加?加多少?」你會立刻翻白眼,對我這些問題感到不耐煩。或者,你會粗暴地抓起我的手並放上一些粗鹽,然後說:「就用你的手心測量。沒那麼難吧。任何東西都能用手量。」你也會說「一湯匙麵粉」,這時,我就得自行領會是一平匙還是一尖匙。更不用說要從你那裡挖到確切的烹煮時間了。你總說:「一雙眼和一把刀,這兩樣東西就足以判斷熟度。」
今早,我用白酒高湯煮蝦子的時候又想了一下,你究竟把你的料理筆記藏在哪裡。那本筆記像顆泡沫在我的記憶裡破裂,有時又會莫名在我燒飯做菜時冒出來。另一天,我正煩惱烤雞裡該鑲什麼肉餡時,想起你有時會在裡面放個小瑞士。當時,我腦海裡浮現了另一個影像:那是一個星期天,你和媽媽坐在床上,背靠著枕頭。那本筆記就擺在她的大腿上。她咬著鉛筆,調皮地敲敲你手上的咖啡碗,提出問題:「那麼,請問大廚,這個要鑲在烤雞裡的塞餡怎麼做?」我感覺到你的不耐煩。你不喜歡「大廚」這個稱呼,翻著白眼,把臉埋進碗裡,嘀咕著:「把一個小瑞士往雞屁股裡塞就對了。」
有多少次,當我愣在鍋子前猶豫不決時,都會想起這個場景?有多少次我幻想著翻閱你的筆記,夢醒了卻還是獨自面對爐火?我似乎又看見它在媽媽的手裡,皮製的封面底下流瀉著規律的字跡,材料、烹調時間、手勢和味道,全都記下了。儘管我一向討厭貝夏梅醬,還是希望能按著躺在紙上的文字一步一步做出你的味道,而不是窺視你的做法。
但你沒有順從我的希望,在你生悶氣的那天選擇了讓它消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