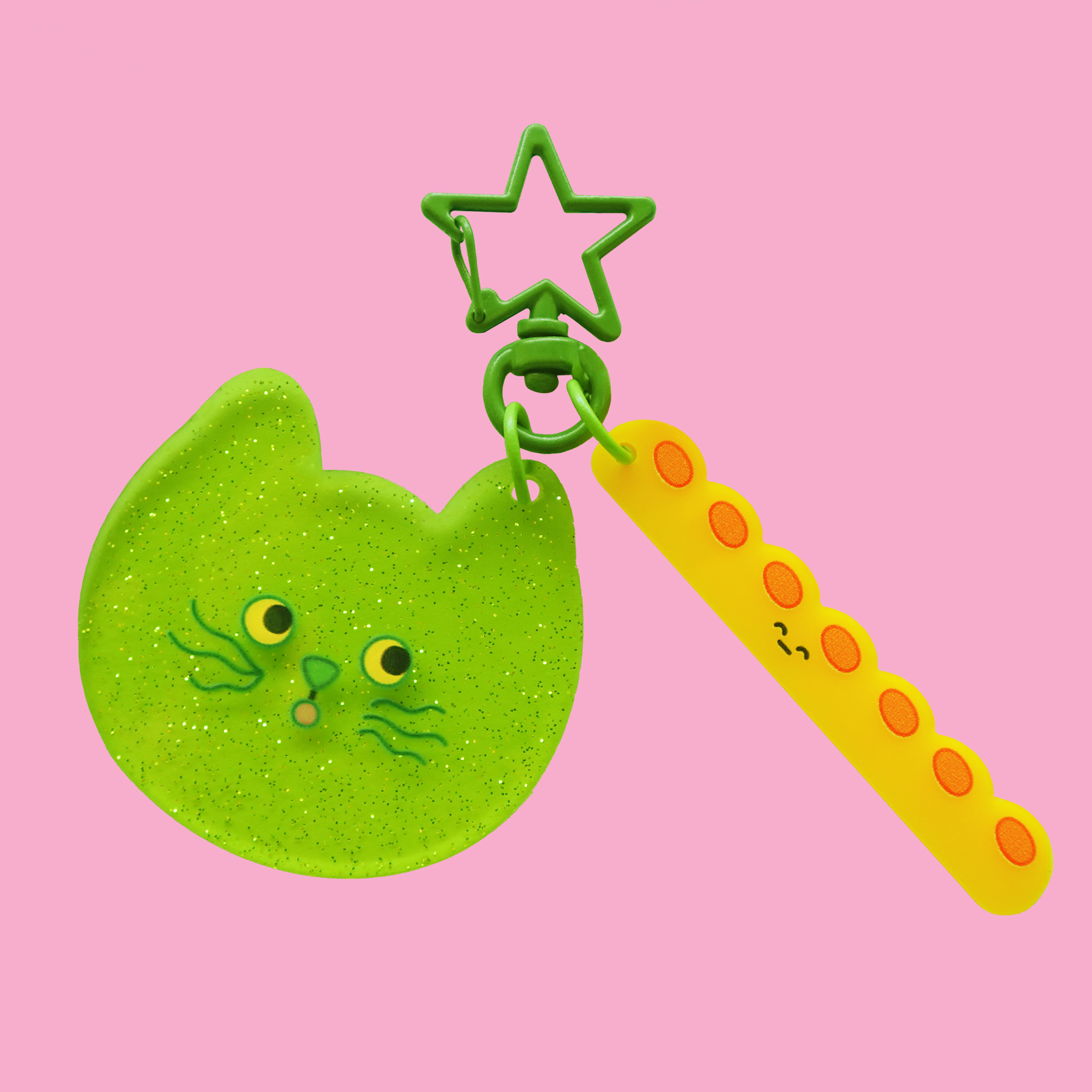4
一八五九年四月一日,他們進入了勒威克港。灰濛濛的天空恐怕隨時會下出雨來,小山丘圍繞小鎮四周,顏色像是潮濕的鋸屑,禿得沒有一棵樹。兩艘彼得黑德公司的「參布拉」號和「瑪麗安」號已經拋下錨,一切妥當,另一艘登第公司的「真愛」號預料明天會到達。一吃完了早餐,伯朗利船長便下船到鎮裡找當地的船務經紀商山姆・泰特,要為船隊補充謝德蘭人船員。森姆納花了整個早上分配菸葉給船員,並照顧艙面水手湯姆・安德生身體的疼痛。到了下午,他躺在下鋪邊讀荷馬邊睡著,到卡芬迪敲門才把他叫醒。卡芬迪說要湊幾個盡忠職守的船員,測試一下當地釀酒業的成就。
「現在這個遠征隊有我,」卡芬迪說,「有跩克斯,我肯定他是他媽的酒鬼上身的異教徒,有黑師傅,是冷靜的顧客,說只喝薑汁啤酒和牛奶,我們等著瞧,還有大鯨魚瓊斯,當然是一條憤世嫉俗的硬漢,所以他對我們來說是他媽的一個謎。總之,我保證這會是一個最過癮的夜晚。」
跩克斯和大鯨魚瓊斯負責划船。卡芬迪說過不停,告訴大家他看過最慘烈的小刀格鬥、幹過勒威克最醜的女人,故事一個接一個。
「我發誓,她的淫水臭到讓人受不了,」他說,「你沒在現場你是他媽的不會相信的。」
森姆納與黑師傅坐在船尾。他離開自己船艙時吃了八格令的鴉片酊(按以前的經驗這分量剛好,足可以讓他外出,又不會在別人眼中像個他媽的白痴)。他享受著海水飛濺在船槳上發出的聲音,以及船槳與槳架互相摩擦發出的吱嘎聲(而且他也高興可以不理卡芬迪)。黑師傅問森姆納這是不是他第一次來勒威克,森姆納確認這是第一次。
「你會覺得這裡是落後地方,」黑師傅告訴他,「這裡土地貧瘠,謝德蘭人又沒有心去改善。他們是農民,有農民的美德,我覺得,不過除此之外什麼都沒有。在島上走走,看看牧場和其他建築物的淒涼景象,你就知道我的意思了。」
「鎮裡的人呢?他們沒有因為捕鯨業而得到一點好處嗎?」
「只有小部分,但是大部分就是因捕鯨業而變得墮落。整個鎮像其他港口一樣骯髒,一樣的邪惡——或許沒有比其他港口差,不過絕對不會比較好。」
「我們要為此感謝他媽的上帝啦,」卡芬迪高聲地回應,「喝杯像樣的酒和一個濕答答的膣屄是一個男人在開始血腥捕鯨前必須的,幸運的是這兩樣東西是勒威克首屈一指呀。」
「他沒說錯,」黑師傅證實,「如果你要的是蘇格蘭威士忌和廉價妓女,你就找對地方了。」
「我很幸運有那麼有經驗的嚮導。」
「你的確很幸運,」卡芬迪說,「我們會教你一些訣竅,對吧,跩克斯?我們會帶你看門道,你可以放心。」
卡芬迪大笑起來。負責划船的跩克斯自從出發後就沒有開口說話,他抬頭凝視著森姆納一會,彷彿是要確定他是誰,有什麼利用價值。
「在勒威克,」他說,「最便宜的威士忌是六便士一杯,一個像樣的妓女要花一先令,你有特殊需求的話可能要兩先令。這就是任何人都需要知道的竅門。」
「你看到了,跩克斯是不多話的人,」卡芬迪說,「但我喜歡胡扯,湊成一組。」
「那麼大鯨魚瓊斯呢?」森姆納問。
「瓊斯是從龐蒂浦來的威爾斯人,從來沒有人聽懂他說的他媽的一個字。」
瓊斯轉身叫卡芬迪閉上他的鳥嘴。
「懂了吧?」卡芬迪說。「他媽的莫名其妙。」
他們在皇后飯店開始,然後移到商務,再到愛丁堡軍器。離開愛丁堡軍器後,他們再到夏洛蒂街上的伯朗太太的娼寮;跩克斯、卡芬迪和瓊斯各自挑了一個女人,便到樓上去,而森姆納和黑師傅在樓下喝黑啤酒。森姆納因服用鴉片酊後都無法辦事,說自己得了淋病還沒有痊癒,而黑師傅則堅持他對未婚妻的承諾,要在婚前守貞。
「可不可以問你一個問題,森姆納?」黑師傅說。
微醺的森姆納視力已開始模糊,凝視著黑師傅,然後點頭。黑師傅年輕而且熱情洋溢,但森姆納認為他略為傲慢了一點。他從來不會公開地表現粗魯或不屑,但是他讓人感到他有某種自信,而那種自信與他的身分不合乎比例。
「好啊,」他說,「當然可以。」
「你在這裡幹什麼?」
「在勒威克嗎?」
「在『志願者』,一個像你這樣的人在一艘前往格陵蘭的捕鯨船幹嘛?」
「我想前幾天晚上我在交誼廳用餐的時候就說過我的情況了——我叔父的遺囑、牧場。」
「那為什麼不在城市裡的醫院找工作?或者暫時做其他事。你一定認識一些人可以幫助你。捕鯨船上外科醫生的工作很尷尬,無趣,薪水又低。通常是需要錢的醫學系學生來當,你這把年紀,有你這種經驗的人是不會幹的。」
森姆納從鼻孔噴出兩股濃烈的雪茄煙,眨了眨眼。
「或許我是一個無可救藥的怪胎,」他說,「或者只是一個他媽的笨蛋,你有這樣想過嗎?」
黑師傅微笑。
「我懷疑兩個都不是,」他說,「我看過你讀荷馬。」
森姆納聳聳肩。他堅持保持沉默,會透露他真實情況的話絕口不提。
「巴斯特給我這個缺,而我接受了。或許又有點魯莽。但是既然我們已經開始,我對這個經驗十分期待。我打算要寫日記、畫速寫,還有閱讀。」
「這航程可能沒你想像中那麼輕鬆。你知道的,伯朗利有很多事要證明——我肯定你有聽過『珀西瓦』號吧。那次之後他還能找到另一艘船,真幸運。如果這次又沒達成任務,他就完了。你是船上的外科醫生,沒錯,但我看過外科醫生被派去捕鯨。你不會是第一個。」
「我不害怕工作,如果那是你說的那種。我會負責我的部分。」
「喔,我肯定你會逃不了。」
「你呢?為什麼到『志願者』?」
「我年輕,家人全去世了,沒有重要的朋友;如果我要活下去我必須要冒險。伯朗利是出了名的不擇手段,但是如果他成功,他可以為我賺一大筆錢;如果他失敗,那不關我的事,而我手上還有時間。」
「以一個年輕人來說,你很精明。」
「我不打算像其他人的下場——跩克斯、卡芬迪、瓊斯。他們已經沒有思考了,不再知道自己在做什麼,或者不知道為什麼這樣做。但是我有計畫。五年後,如果好運的話會快一點,我會有自己的船。」
「你有計畫?」森姆納說,「你認為這對你有幫助?」
「喔,有的,」他說著露齒而笑,展現出對森姆納的尊重,卻帶幾分傲慢,目空一切地說:「我覺得會。」
跩克斯第一個走下樓。他坐到黑師傅身旁的椅子上,放了一個又長又響的屁。二人轉頭看他。他使了個眼色,然後向女侍揮手,再點了一杯酒。
「一先令,已經算不錯了,」他說。
角落的兩個小提琴手開始演奏,一些女生跳起舞來。一群「參布拉」的艙面水手來到娼寮,黑師傅趨前閒聊。卡芬迪再度現身,雙手仍在弄著褲襠上的鈕扣,但是還沒見到瓊斯的蹤影。
「我們的書呆子黑師傅有夠煩的了,是不是?」卡芬迪說。
「他說他有計畫。」
「幹他媽的計畫啦,」跩克斯說。
「他想要當船長,」卡芬迪說,「他不可能的,他對船上的事他媽的一竅不通。」
「船上有什麼事?」森姆納問。
「沒什麼,」卡芬迪說,「一般事務。」
「參布拉」號的人與妓女跳舞,一面尖叫一面在地板上跺腳,空氣中滿是鋸屑和泥煤味,還溫溫的瀰漫著來自菸葉、灰燼和酸臭的啤酒味。跩克斯一臉不屑地看著對面跳舞的人,並要求森姆納幫他點一杯威士忌。「我會簽借據,」他提議。森姆納揮了揮手,便再幫他點了一杯。
「你知道嗎,我聽說過德里的事,」卡芬迪對他說,身體往森姆納靠近。
「你聽到了什麼?」
「我聽說那裡有利可圖,很多戰利品,你有拿到嗎?」
森姆納搖搖頭。
「我們進城前叛軍已經把東西清空了,帶著走,剩下的只有流浪狗和破家具,整個城被洗劫。」
「那就沒有黃金嘍?」跩克斯說,「珠寶呢?」
「我有錢的話還會跟你兩個王八蛋坐一起?」
跩克斯盯著他看了好幾秒鐘,彷彿那是一個複雜的問題,一時間難以回應。
「有真的有假裝不是的,」他最後說。
「我都不是。」
「那麼你有看過重要的血腥場面吧,我敢打賭,」卡芬迪說,「那些最他媽的暴力的。」
「我是外科醫生,」森姆納說,「我對血腥暴力沒有好感。」
「沒有好感?」跩克斯重複著森姆納的話,語氣中假裝著謹慎,彷彿「好感」兩個字帶有女孩子氣,而且略帶荒謬。
「不會被嚇到吧,你可以說,」森姆納迅速地補充,「我不會被血腥暴力嚇到,不會了。」
跩克斯搖搖頭,看著坐在另一端的卡芬迪。
「我自己也不會被嚇到,你呢,卡芬迪先生。」
「不太常,跩克斯先生。我通常覺得自己可以忍受得了些微的血腥暴力。」
跩克斯把酒喝完,便走到樓上去找瓊斯,可是找不到。回到他的桌子途中,和「參布拉」的人員說了些話。跩克斯回到位子後,一個人向他罵了一些話,但跩克斯沒有理會。
「不要了,」卡芬迪說。
跩克斯聳聳肩。
提琴手在拉一首叫〈莫尼馬斯克〉的曲子。森姆納看著那些邋遢又不匹配的男女舞者旋轉並跺腳。他想起印度兵變前在菲羅茲浦跳波爾卡,想起陸軍上校家裡那潮濕悶熱的舞廳,混合著雪茄菸、糯米粉製成的粉底和參雜玫瑰香水的汗味。換了曲子後,一些妓女坐下來休息,或彎身雙手抵住膝蓋喘息。
跩克斯舌頭舔著嘴唇,從椅子站起來左右倚著桌子走到房子的另一邊,來到剛才跟他爭辯的男人旁邊。他停下來不久,彎身靠近男人的耳朵輕聲說了一些他精心選擇的髒話。當男人一轉身,便被跩克斯在臉部揍了兩拳,正要擊出第三拳時,他已經被男人的同行船員拉開並團團圍住。
音樂聲停止,隨之而來的是尖叫聲、咒罵聲、家具破裂聲和酒杯碎裂聲。卡芬迪前往救援,但立即被打倒在地上。現在是二比六,森姆納只是看著,認為自己是醫生,不是來鬧事的,想要保持中立。但是他看見敵眾我寡,便知道他的責任。他把手上的波特啤酒放下,走向鬧事者。
一個小時後,打夠、嫖夠、喝夠的跩克斯負責划船,把人送回「志願者」。船上人員變少了,瓊斯和黑師傅不在,森姆納蜷伏在船尾呻吟,卡芬迪躺在他身邊猛打鼾。沒有月光的夜晚海水墨黑。如果不是捕鯨船上的煤油燈和沿岸的點點燈光,他們什麼也看不見,全被黑暗包圍。跩克斯身體前後擺動,海水隨著他划槳的動作一輕一重地重複著。
到了捕鯨船邊,跩克斯把神智不清的卡芬迪叫醒,然後二人把森姆納拉到甲板上,再合力抬到統艙去。他們要伸手到他的背心口袋裡才找到鑰匙把門打開,他們幫他躺到床鋪上,並把他的靴子脫下。
「這倒霉鬼看來需要一位外科醫生,」卡芬迪說。
跩克斯沒有回話。他在森姆納背心口袋找到兩根鑰匙,想著那第二根用來做什麼。他環顧艙內,發現在藥櫃旁邊的床下有一個上了鎖的行李箱。他蹲下來用食指尖戳了箱子幾下。
「你在幹什麼?」卡芬迪問。
跩克斯給他看了第二根鑰匙。卡芬迪不屑地哼了一聲,並抹去破裂的嘴唇上滲出的血。
「搞不好裡面什麼都沒有,」他說,「只是一些垃圾。」
跩克斯把行李箱拉出來,用第二根鑰匙把掛鎖打開,開始翻看箱子裡的東西。他挪開了一條帆布褲、巴拉克拉瓦頭套、一本裝訂簡陋的《伊利亞德》,另外有一個紅木制的小盒。跩克斯把盒子打開。
卡芬迪輕輕吹了一下口哨。
「鴉片煙槍,」他說,「天哪。」
跩克斯拿起了煙槍,仔細看了一下,嗅了嗅,便放回盒子。
「不可能的,」他說。
「為什麼?」
他揪出一雙防水靴、一個水彩畫箱、一組床單和枕頭套、一件羊毛背心、三件法蘭絨襯衫、一套刮鬍用具。森姆納翻身側臥,並哼了一聲。二人停了下來,看著森姆納。
「看最底下,」卡芬迪說,「最底下可能藏了東西。」
跩克斯把手探進行李箱最底下翻尋。卡芬迪打了個哈欠,伸手去要摳下黏附在外套的手肘上一塊已經乾掉的芥末醬。
「有東西嗎?」他問。
跩克斯沒有回答。用另一隻手伸進行李箱深處,拉出一個骯髒而殘舊的信封袋。他從信封袋取出一份文件,遞給卡芬迪。
「退伍令,」卡芬迪說,過了片刻,他繼續說,「軍事法庭受審,被解僱,無退休金。」
「什麼原因?」
卡芬迪搖搖頭。
跩克斯把信封左右晃動幾下,然後翻轉過來,倒出了一只黃金打造的戒指,上頭鑲了兩顆不小的寶石。
「假貨,」卡芬迪說,「一定是。」
森姆納床頭的牆上有一面長方形的小鏡子,四邊打磨平滑,並鑲有銅製護角,前任住客想必是一位愛慕虛榮人士。跩克斯取過戒指,用舌頭舔了一下,便在鏡面上刮下去。卡芬迪看著他,然後身體靠近鏡子,仔細研究鏡子上的刮痕——像一根從某老嫗頭上拔下來的灰白頭髮。他舔一舔食指,然後抹去鏡面上微細的粉末,讓自己能看清楚刮痕的深度。他點點頭。二人彼此端詳一會,然後垂頭看著看來熟睡中呼吸沉重的森姆納。
「德里的戰利品,」卡芬迪說,「撒謊的王八蛋,為什麼他沒有賣掉?」
「以防萬一吧,」跩克斯企圖解釋,彷彿那答案顯而易見,「他覺得留著會讓他更安全。」
卡芬迪搖著頭大笑,對這個愚蠢的想法感到訝異。
「捕鯨船上充滿危險啊,」他說,「我們之中會有不幸的人是沒辦法活著回家的。這道理很簡單。」
跩克斯點頭,卡芬迪繼續說,「如果一個人在船上死了,當然是大副執行任務,把他的遺物拍賣,歸還給他的遺孀。對吧?」
跩克斯搖頭。
「說得對,」他說,「不過還不要,不要在勒威克。」
「他媽的沒有啦,還沒啦,我還沒有這打算啦。」
跩克斯把戒指和退伍令放回信封袋,再把信封袋塞回行李箱底,並把其他東西歸位。他咔嚓一聲鎖上了行李箱後便推回去床底下。
「不要忘了鑰匙,」卡芬迪告訴他。
跩克斯把鑰匙放回森姆納的背心口袋裡,二人離開船艙,走到艙梯去,在分手時他們停了下來。
「你覺得伯朗利該知道嗎?」卡芬迪說。
跩克斯搖頭。
「只有我們知道,」他說,「只有你和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