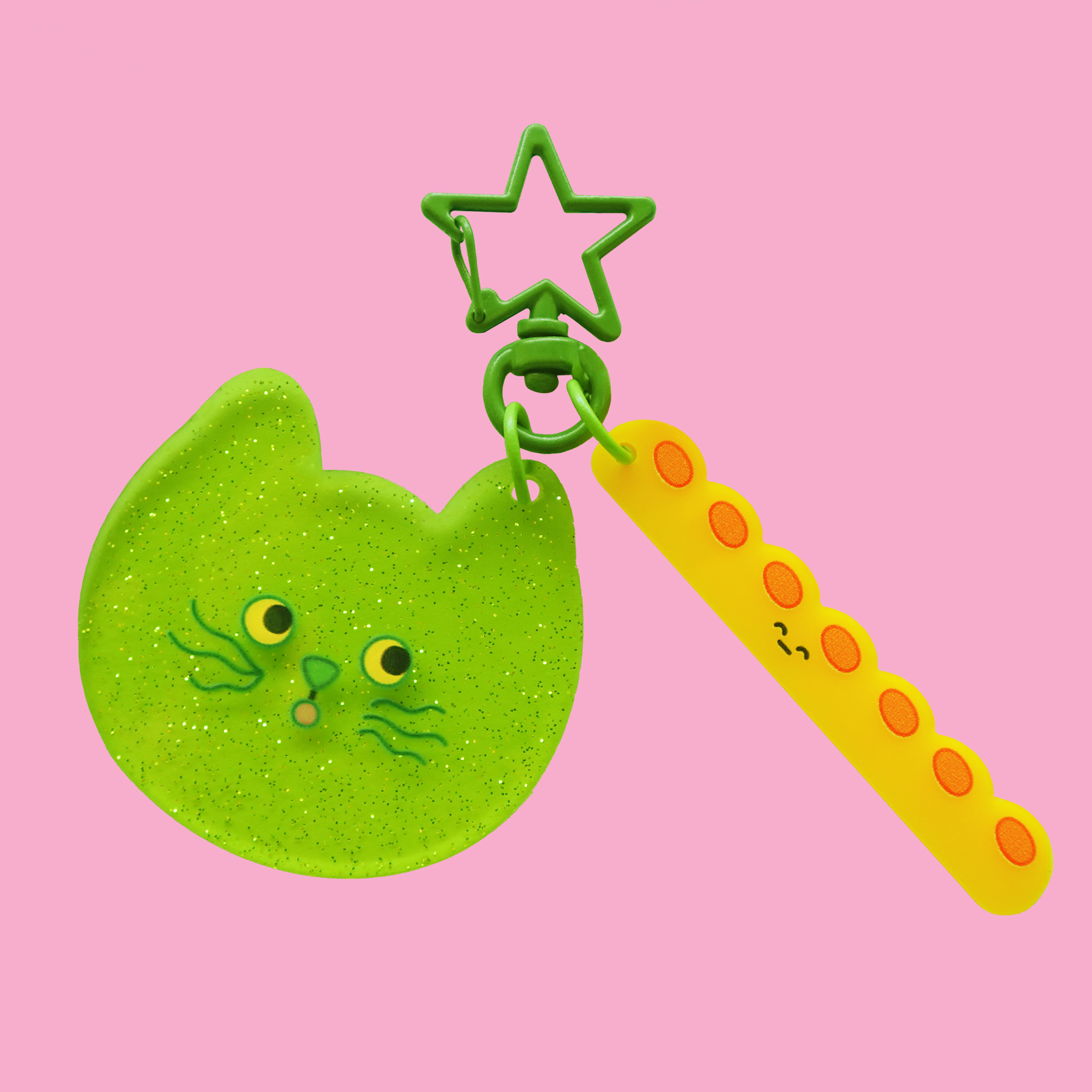天啊,要不是我做了許多噩夢,即便被關在一個堅果殼裡,我都能自命為擁有無限空間的君王。
——莎士比亞《哈姆雷特》
1
我在這裡,在某個女人的肚子裡,上下顛倒,耐心地抱著胳臂,等待、等待,同時揣想我是在誰的肚子裡,為的又是什麼。我閉著眼睛,戀戀不捨地回憶起自己曾經如何在半透明的體袋中游移,作夢似地在我思想的氣泡中飄浮,在我個人的海洋中慢悠悠地翻觔斗,輕輕碰撞圈禁著我的透明邊界;推誠相與的薄膜固然使話聲變悶,也仍和邪惡計畫共謀者的說話聲共振。那時是我無憂無慮的青春。可現在,完全顛倒,一絲一毫自己的空間都沒有了,膝蓋頂著肚子,我的思想和我的腦袋一點空隙也沒有。我別無選擇,我的一隻耳朵日日夜夜都緊貼著充血的壁面。我諦聽,在心中默記,而且我很困擾。我傾聽的是充滿了殺意的枕邊細語,而我惴慄於等待我的會是什麼,以及我可能將陷入的麻煩。
我沉浸在種種抽象概念之中,唯有其間的增殖關係創造出一個幻想的已知世界。我聽見「藍色」,我沒見過,但我想像著某種心理活動,相當接近「綠色」──我也沒見過。我自認是個稚嫰天真的人,不受忠誠和義務束縛,是自由的靈魂,儘管我生活的空間小得可憐。沒有人跟我唱反調或斥責我,沒有姓名或先前的地址,沒有宗教,沒有債務,沒有敵人。我的行事曆,如果它存在的話,只記著我即將來臨的生日。我是,或該說曾經是,一面空白的石板,不管遺傳學家怎麼說;但卻是一面滑溜多孔的石板,隨著時日書寫成長,留白處越來越少。我自認是個稚嫰天真的人,卻好像參與了某個陰謀。我的母親──祝福她跳個不停、響亮地吱嘎叫的心臟──似乎脫不了關係。
似乎,母親?不,就是。就是跟妳脫不了關係。我打從一開始就知道了。讓我召喚它吧,那隨著我第一個概念而來的創造性的一刻。許久以前,幾週以前,我的神經溝自行閉合,形成了我的脊椎以及我數百萬的年輕神經元,忙碌得像春蠶,從牽延的軸突編織出美麗的金黃布疋,也就是我的第一個意念,那意念如此簡單,現在我已有些想不起來了。是我嗎?太抬舉我自己了。那是現在嗎?過於浮誇了。那就是這二者的前因,包含了二者,是某個由接納或純粹的存在所引發的嘆息或狂喜而促成的單一詞彙,像──這樣(this)?太珍貴了。所以仔細想想,我的意念就是將是(To be),不然,就是它的文法變體正是(is)。這就是我原生的概念,而關鍵字在正是。就這樣,奉非如此不可(Es muss sein)為圭臬。意識生命的開始也就是自己並不存在之幻覺的終止,並且現實噴發。現實戰勝了魔法,正是凌駕了似乎。我母親正是在密謀什麼,因此我也一樣,即使我的角色可能反倒會是塊絆腳石。又或者我這個不情願的傻子了悟得太遲,就得扛下復仇的擔子。
但好運當前我是不會埋怨的。從一開始我就知道,在我把包裹著意識的金布攤開之時,我就知道自己很可能會淪落到更差的地方、更壞的時間點。概況已經很清楚了,相較之下,我的家務事就可以、或是應該,略而不論。值得慶幸的地方可多了。我會繼承現代化的條件(衛生、假期、麻醉劑、閱讀燈、冬天的柳橙),居住在地球上一個相對優勢的角落──吃飽喝足、免於疫病的西歐。古老的歐洲,硬化卻相對仁厚,被自己的鬼魂糾纏,受強者欺凌,缺少自信,數百萬不幸之人的選擇之地。我即將身處的鄰里不會是繁榮的挪威──這是我的首選,因為它龐大的主權基金和大方的社會福利;也不是我的第二選項義大利,因為它的當地美食及沐浴在陽光下的頹廢;甚至不是我的第三選項法國,因為它的黑皮諾葡萄和輕鬆活潑的利己心態。我將繼承的是一個不算大一統的王國,由一名受敬愛的年長女王統治,而一個生意人王儲,以他出色的工作、他的靈丹妙藥(可以淨化血液的花椰菜萃取液)、他違憲的干預而聞名,正不耐煩地等待登上王位的那一天。這裡會是我的家,我也只能將就了。我搞不好會出生在北韓,雖然那裡的統治者也是世襲制,卻缺少了自由和食物。
我不但不能被稱為年輕,甚至連出生都還沒,怎麼就能知道這麼多,或是足以知道自己錯了這麼多?我有我的辦法,我傾聽。當我母親楚笛沒有和她的朋友克勞德在一起的時候,總愛聽收音機,她喜歡談話多過音樂。誰能在網路萌生的階段預見到收音機的興起繁盛,或是那個古老詞彙「無線」的復興?我傾聽,在腸胃的咕嚕聲中傾聽新聞,一切惡夢的源泉。我受到自虐的驅使,仔細聆聽各種分析和異議。每小時的重播,半小時一次的綜合報導不會讓我無聊,我甚至能夠忍受國家廣播公司(BBC)的世界新聞以及每則新聞之間傻氣的合成喇叭及木琴樂聲。在漫長寂靜的半夜,我會猛踢我母親一腳,她會驚醒,再也睡不著,然後開收音機。這個活動很殘忍,我知道,可是到了早晨我們倆都會更有見識。
她喜歡聽播客講座和自我成長的有聲書──《品酒常識》,共十五章;十七世紀的劇作家傳記;各種世界經典。詹姆斯・喬伊斯的《尤里西斯》能讓她聽著入睡,我卻聽得著迷。早期她會戴耳機,我聽得很清楚,音波極有效率地從下頜骨和鎖骨向下通過她的骨幹結構,迅速傳進滋養著我的羊水。即便電視也能靠聲音傳達它大半的貧瘠功能。另外,在我母親和克勞德見面時,他偶爾會討論時事,通常都在哀嘆,雖然他們也正在密謀讓世界變得更差。我蝸居在這裡,除了讓身心成長,沒別的事可做,所以吸收一切事物,連最瑣碎的都不放過──而瑣碎的事可多著了。
因為克勞德是個喜歡老調重彈的人。反反覆覆說個不停的人。跟陌生人握手的時候──我聽過兩次──他會說:「克勞德,跟作曲家德布西同名。」他錯了。這個克勞德是個土地開發商,什麼曲子都作不出來,什麼創作也沒有。他喜歡某種想法,大聲說出來,稍後再說一次,然後──有何不可呢?──又再說一次。讓想法持續在空氣中振動就是他的樂趣所在。他知道別人知道他在重複,他不知道的是別人並不喜歡他重複。這種毛病,我是從某次的「睿思講座」聽到的,就叫作指稱的不確定性問題。
底下這個例子可以說明克勞德的說話方式,以及我是如何蒐集資訊的。他跟我母親以電話(我兩端都能聽見)安排了晚上見面。我不算在內,他們計畫要來個──雙人燭光晚餐。我怎麼知道燭光的?因為到了約會的時間,他們被帶入桌位,我聽見我母親的抱怨。每張桌子都點了蠟燭,唯獨我們這一張沒有。
緊接著克勞德氣惱地喘氣,專橫地彈手指,然後是那種諂媚的低喃聲,我猜是來自侍者的,打躬作揖,擦燃了打火機。有了,燭光晚餐。只缺晚餐了。可是他們把沉甸甸的菜單擺在大腿上──我的下腰部感覺到了楚笛那一本。現在我又得聽著克勞德對菜單上的品項高談闊論,活像他是第一個看出這些瑣屑小事有多荒謬的人。他咬著「鍋煎」這個詞。煎就是煎,加個「鍋」字幹嘛?不就為了粉飾俗氣又不健康的「煎」嗎?不用鍋子是要用什麼來煎他的干貝佐辣椒檸檬汁呢?難不成是用煮蛋計時器?在繼續叨唸之前,他又以加強語氣重複了一部分。接著,是他的第二最愛,來自美國的玩意「刀切」。他還沒開口我就默唸著他的開場白,忽然我的垂直方向微微傾斜,我知道是我母親正向前傾,一根手指按著他的手腕,甜甜地改變話題說:「選酒吧,親愛的。選個不一樣的。」
我喜歡跟我母親共飲一杯酒。你可能沒有這種經驗,也可能忘了,一杯好的勃根地紅酒(她的最愛)或是一杯好桑塞爾白酒(也是她的最愛)從健全的胎盤傾注進來。在酒送上來之前──今晚是一瓶尚馬克斯・羅傑桑塞爾──才一聽到拔酒塞的聲音,我的臉上就有被夏日清風愛撫的感覺。我知道酒精會降低我的智力,會降低每一個人的智力。可是,噢,一杯美妙的、令人臉紅的黑皮諾,或是一杯醋栗蘇維濃,讓我在我的私人空間中翻轉滾動,在我城堡的四壁間轉圈,那座充滿彈性的城堡,我的家。至少在我還有更多空間時是這樣的。現在的我只能鎮定地取樂,而等第二杯下肚我就詩興大發。我的思緒一一展開,抑揚五步格,結句行,跨行句,熱鬧非常。可是她從不喝第三杯,這讓我很受傷。
「我得為寶寶著想,」我聽見她說,自以為是地用手蓋住酒杯。那時我心裡就想伸手去抓油膩膩的臍帶,像是在有成群僕役的鄉村豪宅裡拉天鵝絨繩子,用力一扯,叫人來服務。來人!為我們的朋友再把酒添滿!
但沒有,她為了愛我而克制。而我愛她──我怎能不愛?我尚未謀面的母親,我只從內在認識的母親。不夠!我渴望她的外在形體。外表就是一切。我知道她的髮色是「乾草黃」,是以「盤捲的狂亂鬈髮」披散到她「如蘋果果肉的白皙肩膀」上,因為我父親當著我的面向她唸過他寫的詩。克勞德也用一些不夠新穎的詞彙形容過她的頭髮。她心情好時,會把頭髮編成緊緊的辮子盤在頭上,我父親說那是尤莉婭・季莫申科風。我也知道我母親的眸子是綠色的,她的鼻子是個「珍珠似的鈕釦」,我知道她希望能有不只一顆珍珠鈕釦,我也知道兩個男人都很愛她的鼻子,而且都跟她保證過。她聽過許多次別人誇獎她長相美麗,卻還是懷疑,但也因此讓她對男人多了一種天真無辜的魅力,我父親有天下午在書房是這麼告訴她的。而她則回答說就算是真的,那也不是她刻意求索或渴望的魅力。這段對話對他們而言頗不尋常,所以我聽得專心。我父親叫約翰,他說要是他對我母親或是一般女性能有這樣的魅力,他說什麼也不會放棄。我從暫時讓我貼在內壁的耳朵被掀開的波浪動作,猜到我母親刻意聳了聳肩,彷彿是在說,男人不一樣。誰在乎?再說,她大聲告訴他,無論她有什麼魅力,也不過是男人的綺思遐想。接著電話響了,我父親走開去接電話,這段罕見而有趣的對話也就此打住。
回頭來說我母親,我口是心非的楚笛,我所渴望的蘋果果肉般的胳臂、胸脯和綠眸,她對克勞德難以解釋的需求早在我的第一個知覺,我原始的正是出現之前就存在了,而且她經常跟他說話,他也是,枕邊細語,餐廳細語,廚房細語,好似他們兩人都疑心子宮也有耳朵。
我以前認為他們的謹慎不過意味著普通、情愛的親暱,可現在我確定了。他們讓話聲輕如羽毛般通過聲帶,是因為他們在籌謀一個恐怖的計畫。萬一哪個環節出了錯,我聽見他們說,他們的人生就毀了。他們相信如果要執行下去,就應該快刀斬亂麻,而且越快越好。他們囑咐彼此要若無其事,耐著性子,提醒對方計畫失敗的代價,每個階段必須要環環相扣,只要有一個環節出錯,整個計畫就會「像落伍的聖誕樹燈泡一樣悽慘」──這難以理解的譬喻出自克勞德,他說的話鮮少會這麼晦澀難懂。他們的計畫嚇壞了他們自身,因此從沒辦法直截了當地說,而是包裝在低聲細語中,充滿了省略和委婉的說法、嘟囔不清的置疑,緊接著是清喉嚨,俐落地改變話題。
上週某個炎熱的晚上,我以為他們倆早就睡了,誰知我母親突然對著黑暗說話,就在樓下我父親書房裡的時鐘跑到黎明前兩小時的時候。「我們做不到。」
克勞德立刻就說:「我們可以。」然後,思索了一會兒。「我們可以。」